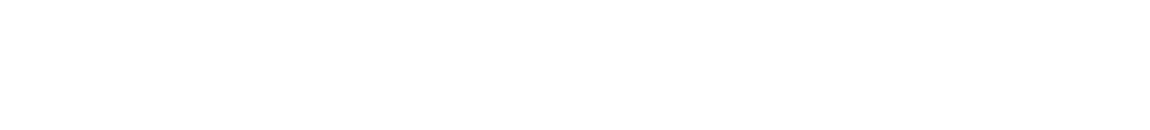| 注释:
①参见“双11快递货车高速上起火,4500多件快递‘葬身火海’”[EB/OL].[2017-12-24].http://money.163.com/17/1113/15/D34QHQVJ002580SN.html.
②比如,网购合同中当事人一方欠缺行为能力是否会影响合同效力;网站标价错误时,网购合同是否成立及是否适用意思表示错误规则;通过电子代理人订立网购合同时,电子代理人之法律地位等问题。
③比如,徐学鹿.析“民法商法”化与“商法民法化”──再论“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6):19;张谷.中国民法商法化举隅[J].金融法苑,2005(1):74.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27. 另外,《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2条也表达了这种思路。
⑤严格来说,送付之债与寄送买卖实际不是一个概念,送付之债是指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不一致、履行地在债务人所地而履行结果地在债权人住所地或其指定地点的债务,它涵盖一切债务,不限于买卖之债。但寄送买卖仅指履行地在卖方住所地而履行结果地在买方住所地或其指定地点的债务,它是送付之债的下位概念。但是,鉴于本文通篇都在论述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问题,所以下文中以上两个概念将会混用。
⑥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Ⅱ——契约之内容与消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16. 对于送付之债的概念,有观点认为,它是指以债务人所在地与债权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为履行地之债务,但这个值得商榷。例言之,买方住所地是北京,卖方住所地是武汉,如合同约定在北京交货,就属于赴偿之债。但是,如果买方因北京收货不方便,让卖方将货物送到其在长沙的仓库,按照上述概念,这是送付之债。但不论北京或者是长沙,都是买方所指定,仅仅因地点不同,就将两者区别对待,这显然不太合适。况且,送付之债与赴偿之债最大区别是:风险转移的时点不同。对于赴偿之债,风险在债权人住所地转移;对于送付之债,风险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转移。据此,同样是卖方委托独立承运人运输,如果收货地点在北京,那么风险在北京转移;如果收货地点在长沙,那么风险货交第一承运人时就转移。但这一结论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区分送付之债、赴偿之债以及往取之债的标准其实有两个:一是“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是否合一”,二是履行地。当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分离时,属于送付之债;当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合一时,属于赴偿之债或往取之债。在“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合一”的前提下,根据履行地是在债权人住所地或债务人住所地,可区分赴偿之债与往取之债。另外,虽然有学者认识到了送付之债是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分离之债,但同时也认为,送付之债是履行地为债务人住所地、履行结果地为债权人住所地之债。但如此会有盲点,比如,当履行地与履行结果地分离时,买方住所地本是北京,却让卖方将货物运到长沙,依前述概念,这种债就不属于前述三种中任何一种。但从理论上来看,不论是运到北京或长沙,风险转移时点都应是货交第一承运人之际。分类的意义在于法律效果上区别对待,既然两者在法律效果上不应区分,那么就无分类之意义。所以,不论履行结果地是否是债权人住所地,只要是由债权人指定,都是送付之债。
⑦依《合同法》第288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所以,约定地点(收货地址)应视为运输合同的必要条款,如买方不告诉卖方收货地址,那么运输合同根本无法成立。
⑧这一点从《德国民法典》第447条第1款也可以看出。该条第1款规定:“出卖人根据买受人之请求,将买卖物发送到履行地以外的地点的,一旦出卖人将物交付给运送代理人、运送人或其他被指定执行发送的人或机构,风险就转移给买受人”。该款中,买受人收货地在履行地以外,只能视为履行结果地。可见,买卖双方对收货地址之约定未必就是对履行地之约定,两者是不同概念。另外,可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8.
⑨根据《合同法》第141条,只能通过《合同法》第61条确定履行地,排除了《合同法》第62条第3项的适用。参见田朗亮.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案例适用(增订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5.
⑩《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11当然,卖方退款后一般会与物流公司交涉,请求物流公司赔偿损失,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风险负担无关,在此不赘。
12对于送付之债的概念是存在争议的。韩世远认为,它是指以债务人所在地与债权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为履行地之债务。但本文不敢苟同,具体理由见注释⑤。另外,对于这两种观点之评释可参见注释⑥,陈自强书,第316页。
13该款规定:“但是,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当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货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置时,风险转移”。
14对于比较法解释方法,梁慧星教授曾举一例:《民法通则》第122条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系参考美国严格责任判例法与欧共体关于产品责任的指令,因此对于该条使用的语词概念也应参考美国法与欧共体指令来解释。该例与本文情形异曲同工。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36.
15寄送买卖是指卖方仅有义务办理货物运输,无须负责运输过程而仅将货物移交给承运人即可。这一案例中,卖方有义务办理运输,且须负责甲乙之间之运输,但不必负责乙丙之间之运输。所以,就甲与丙之间,该买卖不是寄送买卖,只能说在乙丙之间该买卖是寄送买卖。
16法释[2009]1号第3条也体现了这一思路。该条规定:“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
17题目如下:“甲、乙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由甲代办托运。甲遂与丙签订运输合同,合同中载明乙为收货人。运输途中,因丙的驾驶员丁的重大过失发生交通事故,致货物受损,无法向乙按约交货。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A、乙有权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B、乙应当向丙要求赔偿损失;C、乙尚未取得货物所有权;D、丁应对甲承担责任”。该题给出的标准答案为A,因为题目的立意在于:债务人甲虽然因为第三人丙导致货物毁损而不能向债权人乙按约履行义务,但《合同法》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据此应当选A。参见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解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51-252.
18比如,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J].中国法学,1999(3):25;王利明.民法典合同编的修改与完善[EB/OL].[2018-01-24].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f099fba0102x8vq.html.
参考文献:
[1]韩世远.中国合同法与CISG[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3.
[2]范健.走向《民法典》时代的民商分立体制探索[J].法学,2016(12):25.
[3]陈自强.民法讲义Ⅱ——契约之内容与消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15.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76.
[5]Secretariat Commentary on Article 79 of Draft Convention(Article 67 of Official Text), Paragraph 4, Official Records, p.64.
[6]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评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2-293.
[7]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87-489.
[8]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05.
[9]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50.
[10]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227.
[11]王洪亮.债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7.
[12]朱晓喆.寄送买卖的风险转移与损害赔偿——基于比较法的研究视角[J].比较法研究,2015(2):30,40.
[13]Staudinger/Magnus,Art.67 CISG,Rn.1.
[14]朱景文.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6.
[15]王慧.国际贸易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9,134,250,251.
[1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29,277.
[17]丁国民,张积储.国际寄送买卖的风险负担规则及适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30.
[18]李洁.网络购物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问题探析[J].经济问题,2015(6):21.
[1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61.
[20]Dionysios Flambouras,Transfer of Risk in the Contract of Sale Involving Carriage of Goods,in International Tradeand Business Law Annual,Vol.VI,University of Queensland,2001:87-149.
[21]杜景林,卢谌.德国债法改革:《德国民法典》最新进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4.
[22]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2011/0284(COD)).
[23]米健.比较法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3.
[24]沈达明,冯大同.国际贸易法新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109.
[25]许明月,王晓东,胡瑞娟.国际货物运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6.
[26]吴益民.国际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80.
[27][英]约翰·F·威尔逊.海上货物运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27.
[28]曾立新.海上保险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5.
[29]陈立虎.当代国际贸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3.
[30]周江洪.《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与适用[J].清华法学,2012(5):157.
[31]韩世远.他人过错与合同责任[J].法商研究,1999(1): 40.
[32]齐恩平,王立争.论第三方物流中标的物风险负担[J].现代财经,2008(7):70.
[33]于韫珩.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16(4):79.
[34]郭峰.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J].中国法学,1996(5):44.
[35]徐强胜.商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1.
[36]U. Magnus,The Remedy of Avoidance of Contract Under CISG-General Remarks and Special Cases,25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423(2005-2006).
[37]张谷.中国民法商法化举隅[J].金融法苑,2005(1):74. |